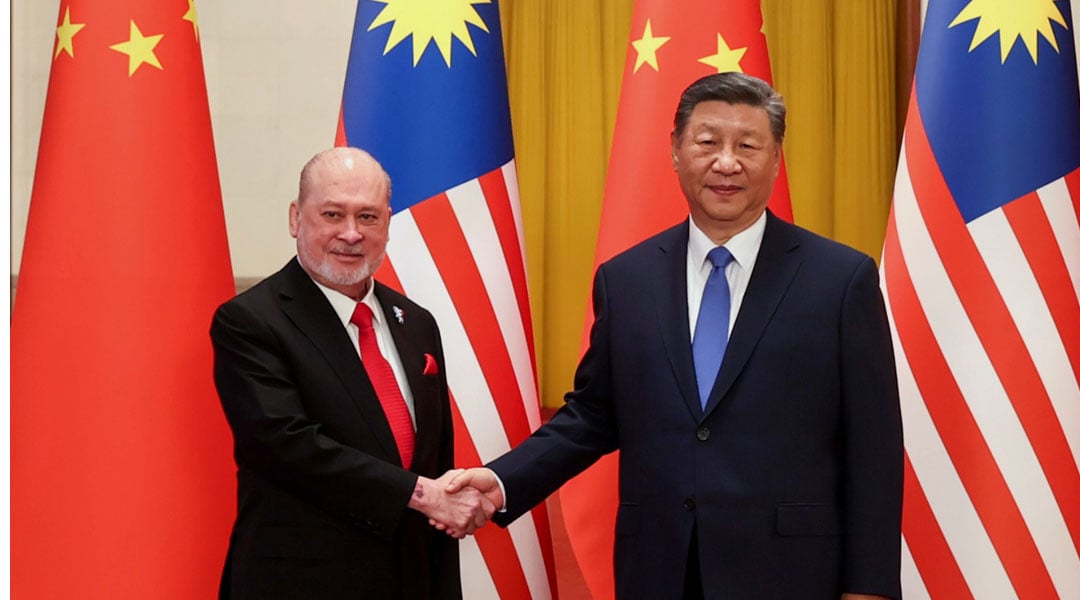文/林武灿
如果要说律师界里才华洋溢,不只能言善辩,而且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出书表达本身经历与情怀的人,我首推聚文学、法律与政治于一身的李国良律师、小说家(1927-1992)。
李律师诞生于吉打州亚罗士打,1950年在墨尔本求学。他在实习时期就开始写故事和小说,这些作品后来就成为以后他书中的素材。他可以说是我的老学长,于1952年在伦敦林肯法院毕业为法律辩护士(我是1984年毕业的)。他于1954年回国,过后在槟城开始执律师业至终年65岁,据知是心脏问题。虽然他如愿以偿地脱离了帝国和回归马来西亚,但是在往后参政的日子里,他才发觉到在本邦的现实社会里,其实并不容易摆脱本邦种族政治的框框而有所悲悯。
李律师有着多姿多采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第四代的海峡殖民地华人,母亲则集多元种族即泰、华与马来文化于一身。他的内祖父是吉打苏丹的秘书,外祖父则是吉打的华人甲必丹。他形容自己是持怀疑态度的禅宗佛教徒,并倾向于密宗及一些兴都象神元素。其实这倒也反映了早期佛教在吉打州传播的影子。
从三十至四十年代,他的教育经过了4个时期的华文、日文、英文、和马来文的教育制度。这造成他对多元文化的觉醒和敏感,对他日后无论是在写作或参政方面,都可以说是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李先生皆以高素质的英文写作,最著名的是《三十二个马来西亚故事》(2005),收集了早期他在墨尔本大学实习时所写下的作品。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太阳下的静音》(1981),托出了在东南亚化文下的人性关系,有父子、朋友、与爱人之间的关系。他的第二部小说《天空中的花朵 》(1981),表达了当时本邦的华裔同胞,如何去适应一个陌生环境的小地方,其中也附带些宗教的小插曲。他的作品富有创造性与幻想力,不时揭示社会不公与不正义的一面。这和他在法律和政治上偏向于帮助劳工和被欺压的一方,有着一种一致性或连贯性的纽带。
2003年,李国良往生11年后,他的遗孀李夫人才出版了他所写的手稿叫《伦敦不是属于我的》。这本著作刻骨铭心地描述了作为殖民地子民的他,身处帝国大都市的文化中在心理上的予盾和感受。他以本身在伦敦和巴黎的生活经验写成了这篇洞察力细微的小说,企图通过西方大文豪如莎士比亚的情怀与文艺诗歌的手段,忽隐忽现地以第一人称,诉说着当时生活在帝国的书中主角之孤独,浪漫的情景和内心的思绪。
书中表达了作者对本身种族身分的纠结,对一个正趋没落的帝国主义文化之有价值的描绘,并涉及肉欲、性取向(同性恋/异性恋)、娼妓、殖民俱乐部、婚姻、家庭、宗教与暴力(心理与政治上的) 的课题。当时他是身在地中海一带写下此书的,时为1954年即国家独立前3年。因此西方文学界公认李国良为马来西亚人以英文写小说的第一位或鼻祖,虽然此书一直拖到2005年才出版面世。
李先生曾于1959年在劳工党旗帜下,中选槟城巴当哥打区州议员,当时亦有另外6名劳党州候选人也一起打进槟州议会。劳党注册被吊销后,他于1974年又以人民党身分竞选巴当哥打区州议席,与社会正义党的陈朴根律师,以及行动党的邱思和,围攻寻求蝉联的国阵/民政党的林苍祐医生却不果。若把他们这3位候选人所得的选票加起来,却比林医生的得票还要来得多一些。
1985年, 在我实习期满后,必须向槟城高庭请愿为大马合格律师时,代表我向高庭请愿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知名与资深的李国良大状师。在获得当时的高庭法官拿督再汀(1988年擢升为联邦法院大法官并受封敦)赐予的庭令批准与训示后,我还有幸得到李前辈凑上前来亲自为我披上律师的大黑袍,令我深为感动和感恩。
我还记得李前辈告诉我,他是槟城第一家用上电脑的律师楼,当时我也注意到在法庭桌上放着的,正是一本他爱不释手的电脑书籍。在他的启示之下,我也满怀信心地跟随着他的步伐去电脑化我的办公操作。
李先生于1992年写下他最后的一本书 《死亡是个仪式》。仿佛对死神将会来临有所预测似的,他竟然在同年去世。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我驾车经过车水路时,我瞄到身穿黑长裤和半卷起白长袖的李律师,正好在路旁享用一杯小贩售卖的现绞甘蔗水,地点就在拜吉小学篱笆不远处。
李先生出殡那天,我出席了他家属在丹绒武雅住家前,以佛教仪式为他举行的肃穆丧礼。当时我看到一位站在比较疏远处并戴着墨镜、神情木然哀伤的妇女,神秘兮兮地默默观看着整个过程,心想这又会是谁呢?
仪式走到最后,当司仪喊着“亲戚朋友谁还没点香的请出来点香”时,她才凑近灵前点支香来作个永别。这时我听到旁边有人在说,这就是他已离异并且去了澳洲多年的前妻。我心中默念:李前辈,您应该可以好好安息和往生极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