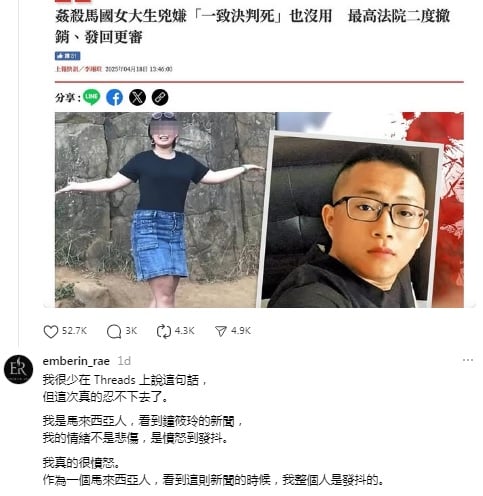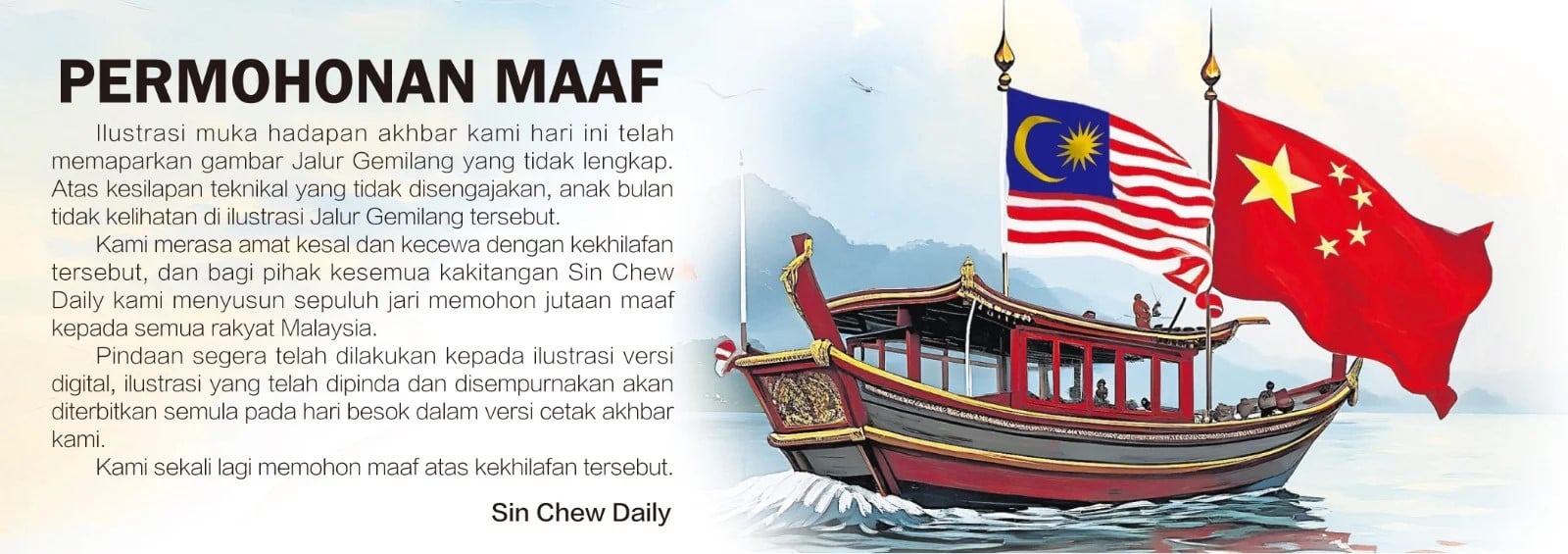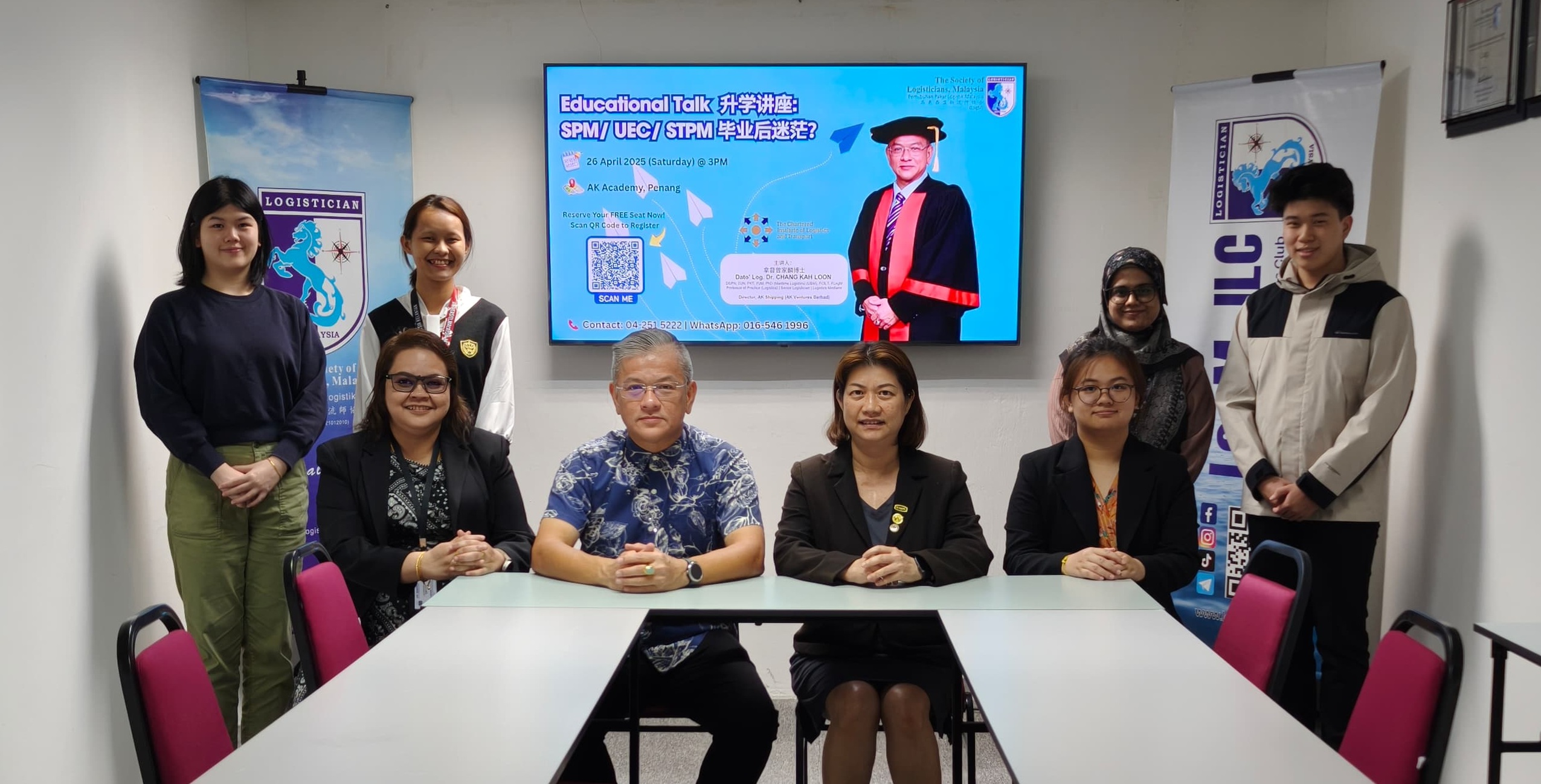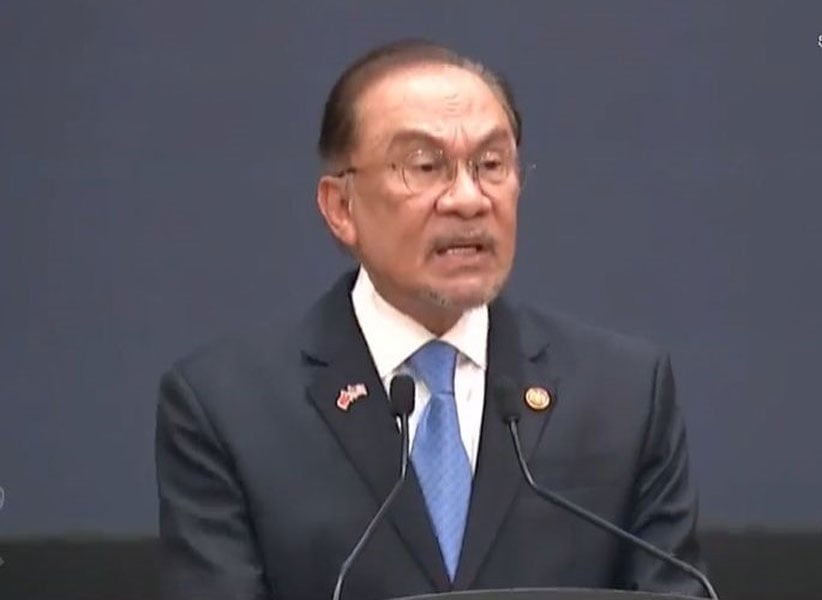文/林武灿
像我国这种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度里,司法具有能力去制衡行政与立法的操作,以确保另两个政府机关依法行事,不能越权或滥权(参见国家宪法第121(1)条款)。因此,确保司法制度的公正不阿,通过俗谓“王公犯法与庶民同罪”,或西谚语所说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原则,它将能使司法有望成为民主社会的安全网。或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果如影相随,正义从而得以伸张。
我国的司法制度不像美国那样设有法官的选举,而是跟随英国的法官由政府委任制,并根据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而进行。然而我国也不像英美那样设有陪审员制,由他们去以事实作衡量后投票来裁决案件,而他们的法官只是提供法律和程序的指导而已。在我国都只有法官/庭主或推事本身(通过高庭/低庭)去进行对事实的衡量和法律的适用来作裁决,没有什么陪审员的。
我国司法职位的委任,退休和罢免是根据国家宪法条款来进行,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的任职安全是有所保障的。司法的公正要求司法官员在政治上中立,同时也不以多数人的偏好作考量,而是在不偏不倚,兼听则明的情况下,耐心地聆听和掌握了事实与在庭上所提供的证据后,客观地以法律加以使用和衡量,并进行判断和裁作。在这里,法官个人的主观和偏好必须被搁置于一旁,并必须公正廉明地去依法依逻辑去主持公道和正义。
任何受影响人士,可入禀挑战法官听审有关案件,如果有证据证明该法官不适合听审是基于利益冲突,例如他曾受聘为两造其中一方的职员,他或他的亲属会因判决而受益,或者他曾经讲了一些有偏见或对当事人或其所属群体不利的话,从而要求他回避及更换法官。不时也出现了因此而更换法官的决定。
在依法律依程序公开与透明审讯的大前提下,如果法律的字眼是明明白白的,法官根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必须严格地根据法律的意思下判断。如果法律的字眼模糊,模棱两可,或甚至是意义多重的话,那么法官则有了比较大的空间去阐释法律,在掌握语义学的本领下,以他本身对有关法律意思的看法来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甚至有权审查到底国会通过有关法令时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当时国会讨论的背景来作考量因素,并在其判词中如是说明。
司法公正并不允许法官以政治立场或因为时下的普遍民意去审视案件。譬如在劳方资方、生意股东、房东房客或夫妻之间的纠纷,基于个人情感如同情或偏好而行事。历史上发生过的在1972年内安法令下扣留犯人人身保护令的申请多项个案中,法官也只能以不吻合扣留程序而放人,而不是也不能去过问内政部长对扣留犯“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看法是否属实。基于这是一个公众政策的问题,而法官也只能如是衡量轻重。因此,它从来就很难给公众人士机会去挑战内阁部长对被扣留者是否真的有威胁到公众的安全,部长对大众利益的看法,或去质疑他扣留决定的真正动机。
至于司法是否会有创意性呢?创意或否也只能看法律条文是否清晰,若是,昭然若示别无他途;若否,法官的创意空间就越大,因为他就是诠释法律条文的判官。因此,往往就会出现一些看起来似乎比较开放、自由和进步的判决,而另一些则显示好像是比较保守和落后的判决。其实有创意的法官在下判时,应该能够促进法律的发展(因为有良好的司法判列),以及对法律的良好诠释与加予使用(立竿见影)。
司法检讨的请愿依旧是对立法和行政机构(包括半司法机构诸如工业法庭)的一种有效制衡方法,而在1956年政府程序法令下,在我国人民也可以起诉政府和政府部门。而后者若不依法或滥权,不时也是有败诉的案例。司法也可以检讨宪法下所赋予部长或政府要员如总检察司的审慎权力,它是否应用得恰当,亦可追究。我们不像一些极权或独裁国家,政府永远是对的,不可被起诉或真的被起诉了,政府也绝对不会败诉的。
当然司法并非那么神奇的具有阿拉丁神灯般的魔力,可以任意地去使唤山门开关,而司法官员的个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人生经验、思想体系和社会价值观,也无形中在影响着他的看法,因为他们毕竟也还是人。一份由英王约翰于1215年颁发予英国人民的政治与公民权力大宪章(Magna Carta)里,有以下这么一句话能够成为司法公正的永恒座右铭:“我们将不会卖给任何人,我们将不会否决或延迟任何人的正义或权利”。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就曾经有过没有法律的正义,如今也有了依据法律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