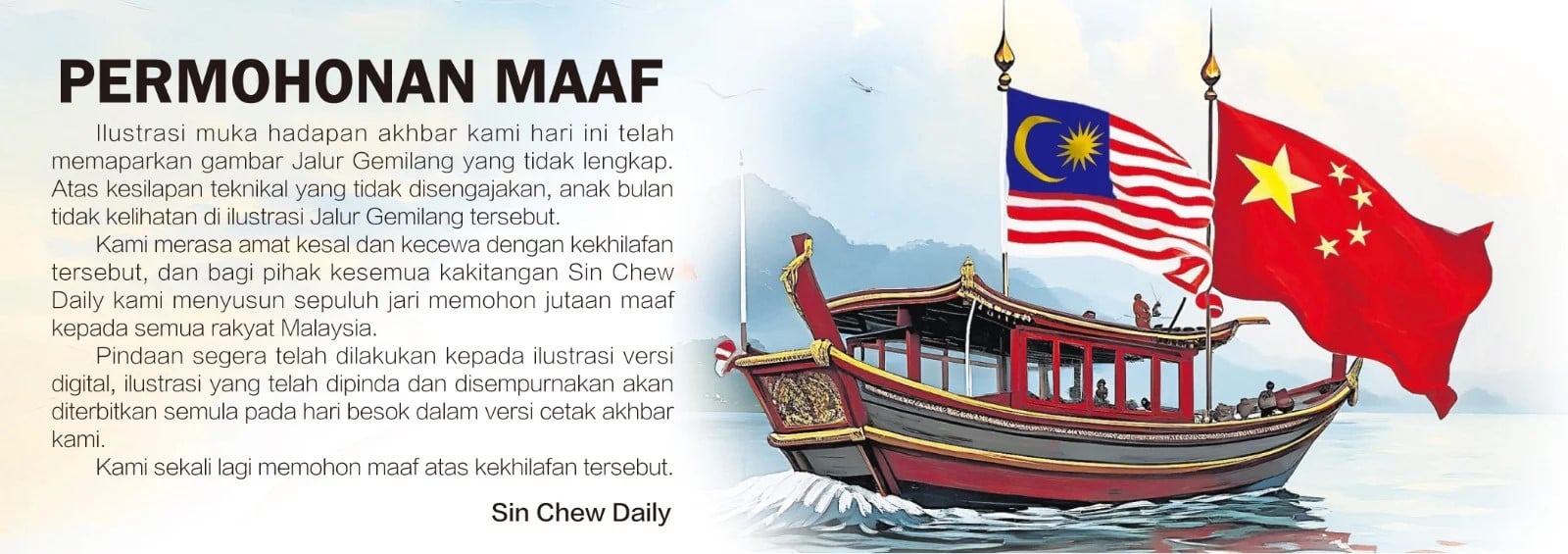沙迪史与当地长老努润伊斯兰了解罗兴亚人的困境。
报道/摄影:何湘云
持有联合国难民署(UNHCR)难民卡的罗兴亚人,虽然并不能堂堂正正的在我国工作,但是长时间生活在这里后,他们当中不少人不只是在这里“成家”也“立业”,甚至有人自己接工,承包工程自己做“老板”。为了生活,他们承包“脏”、“乱”和“危险”的活儿来做,以更低的价来接工,再找同乡一起出去开工,抢本地人饭碗。
在大马已经有26年的阿敏(40多岁),能口操流利的马来语。他说,他一直很感恩大马政府让他落脚,但是他们都是血肉之躯,持着一张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所发出的难民卡,根本不被允许在大马找工作。
他说,持有难民卡,一般的大企业建筑公司都不会聘用,虽然如此,为了温饱肚子,他还是在一些建筑工地学扎铁。
询及他在缅甸是哪一行业出身,他说,在缅甸他是一名稻农,现在来到大马就变成了建筑工人。
所以学一门粗工,往后四海为家,他与家人都有一口饭温饱肚子。
阿敏说,像他们这些无国籍的民族,没有人愿意当他们的雇主,所以他本身只有在乡区小地方承包一些小工程来做。
“如果工程需要更多的人手,我会叫3个亲友一起工作,把赚到的钱都平分给他们,一天的工资大约70令吉至100令吉不等,以日薪计算,因为不是每一天都有工作。”
他无奈的说,假如工程只足够一个人工资时,他迫不得已也要先想想家里的妻子和儿女,他也迫以无奈的牺牲他人,一个人承包起整个工程。
“我可以把自己给饿死,但孩子和妻子都需要食物裹腹。”
他坦诚说,在大马落脚多年他娶了一名罗兴亚女子为妻,并育有3名年龄7岁、9岁和10个月大的孩子。
他计算说,一个家庭一个月的费用需要2000令吉至3000令吉,单是屋子租金已经600令吉,包括水电费。
“2个孩子的补习费160令吉、车费回程一趟每月50令吉,包括学费等,都需要350令吉。”
他说,在没有工作时,让他相当无助,但也没办法,只有向同乡借钱。
暴乱中亲人失散身亡 举目无亲下单独来马
“宁做太平狗,莫做乱世人”。阿敏透露出“无根人”的暗淡人生,在他一双空洞而迷茫的眼神里透露出,有家人的地方,四海都是家。
他想起缅甸这个不像家的地方,双眼通红的指出,忆起缅甸让他心碎,家园和教堂都被神手铲为平地及烧毁,家人也在暴乱中四处逃散或身亡,在举目无亲之下,1997年单身一人来马。

为如何养活妻儿发愁
莫哈末拉欣(32岁)说,他与妻子育有3名孩子,他在大马工作和居住已经有10年了。
他表示,现在他们几个友人都对着家庭经济发愁,因他们是难民身份,要到外找工作很艰难。
原任峇眼达南州议员沙迪史
抢饭碗引本地人不满 建议制定难民政策

原任峇眼达南区州议员沙迪史指出,在峇眼达南州选区,有罗兴亚人在当地经营生意,甚至与大马人承包商抢饭碗,引起本地人的不满。
他举例,3000令吉的承包小工程,他们出价1500令吉把工作抢走。
他说,本地承包商买建筑材料和申请证件都需要缴税给政府,自然成本比较高,但是罗兴亚人用自己的途径逃过缴税,可以开出更低的价。
沙迪史指出,峇眼达南州选区约有1000个罗兴亚家庭,一个家庭有5至6个成员,所以估计计算最少有5000人。
他认为,大马应该有难民政策,这样政府才能更好的管制罗兴亚人的问题,比如限制工作的领域,居住的地方,包括教育等。 他说,目前大马并不是《难民公约》签署国,并没有义务接收罗兴亚人。我国是因人道主义敞开大门协助他们。

对付犯法罗兴亚人
他说,也因为我国没有“难民政策”,导致执法单位变成“无牙老虎”。罗兴亚人在他们聚居的村内组“罗兴亚村”,违法在公路上驾驶,甚至不用纳税给政府就在大马经营起小本生意,只要他们一亮出保命符(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卡),执法单位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他说,移民局的法令很弱,无法针对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卡者采取行动,包括逮捕、拘留及提控等,所以对方怎样犯错执法都拿他们没办法。
他说,难民事件已经造成了大马的负担,但是联合国难民署没有采取任何对大马有利的行动,所以我国必需在不影响难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下制定“难民政策”。
他直言罗兴亚人在我国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交通,但是交通车卡的拥有人则是本地人,驾驶人士竟然是罗兴亚人。
威省市议员黄咏玮
应给罗兴亚人更好庇护 别让他们活得像过街鼠

威省市议员黄咏玮认为,我国政府应该给罗兴亚人更好庇护,而不是让罗兴亚人活得像过街老鼠。
“持着难民卡要工作不能,也没有设定的地方安置他们,让他们四散到大马各社区和乡区,日久肯定会产生一些民生课题。”
他说,当生活把人迫到眉间时,为了一家人温饱肚子,想歪路了就走旁门左道去犯法。
他建议政府允许一些领域聘用暂居大马的罗兴亚人工作,在工资方面也有一个可让他们糊口养家的价码,而不是使用执法将他们逼入死胡同。
他提起外劳犯罪的事项,罗兴亚人都会被牵连在内,在大马国家外籍人士犯罪可以被遣送回国,但是如果罗兴亚人无法回自己的国家之际,其他国家也把他们当人球踢来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