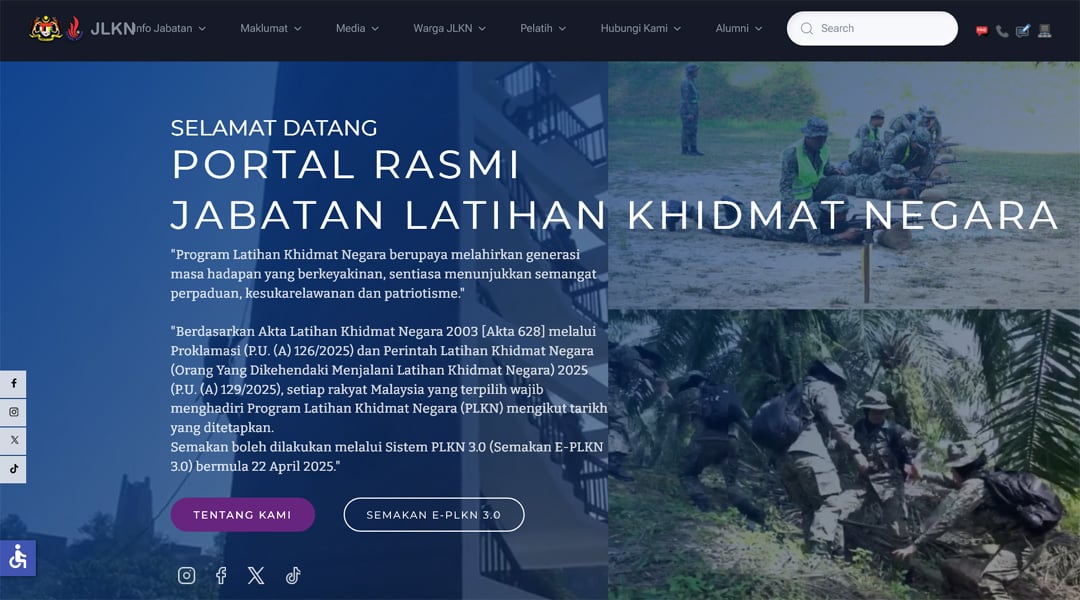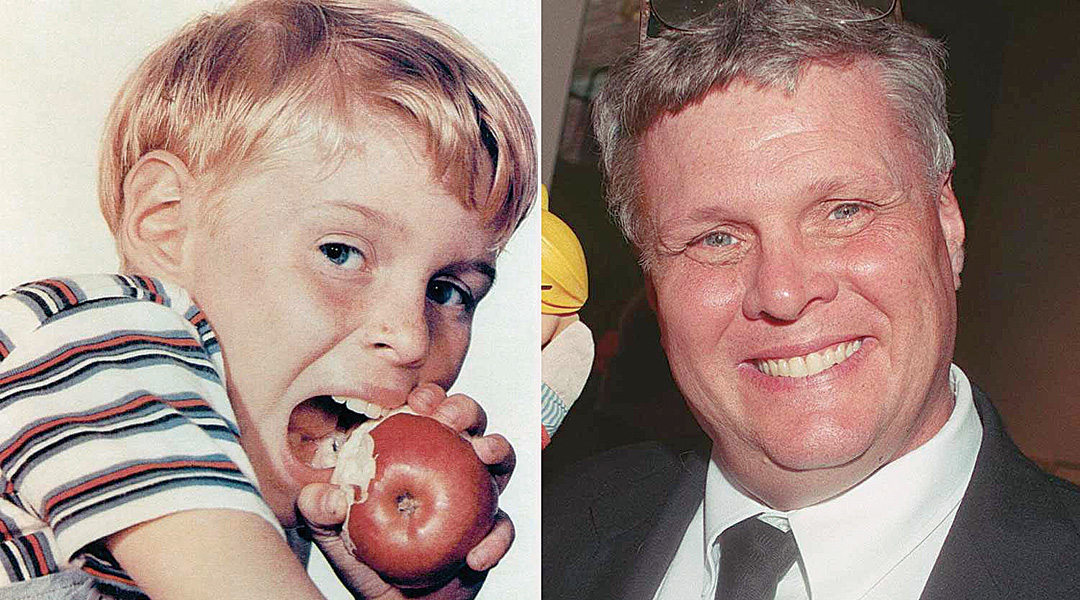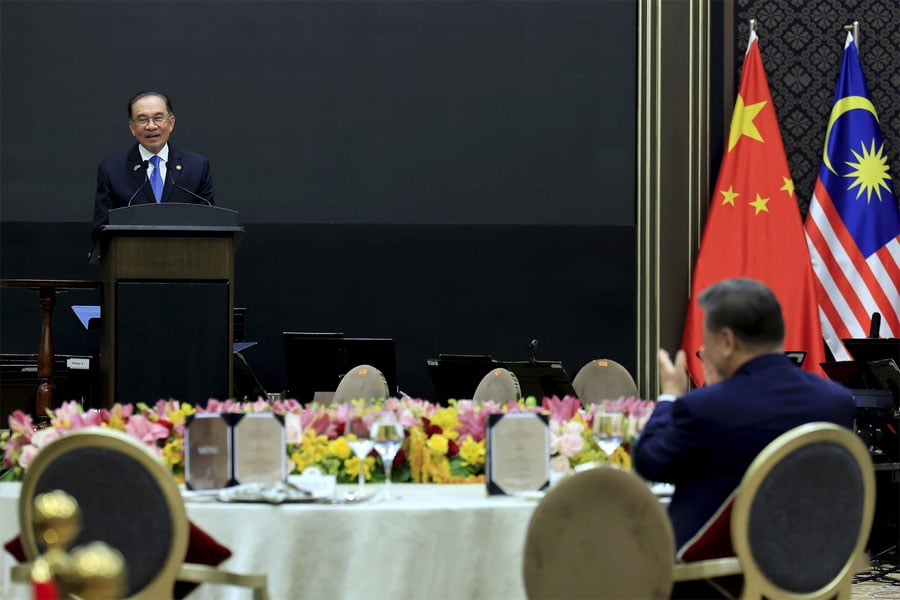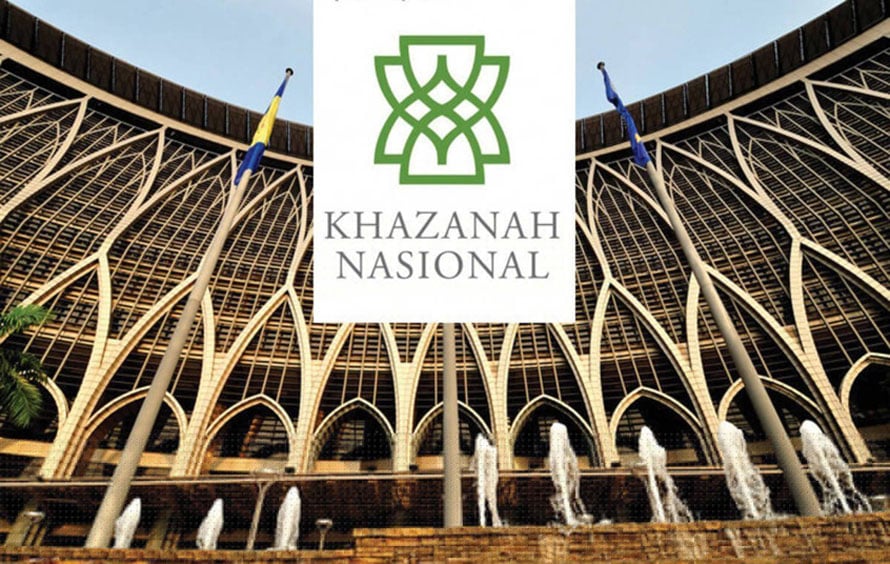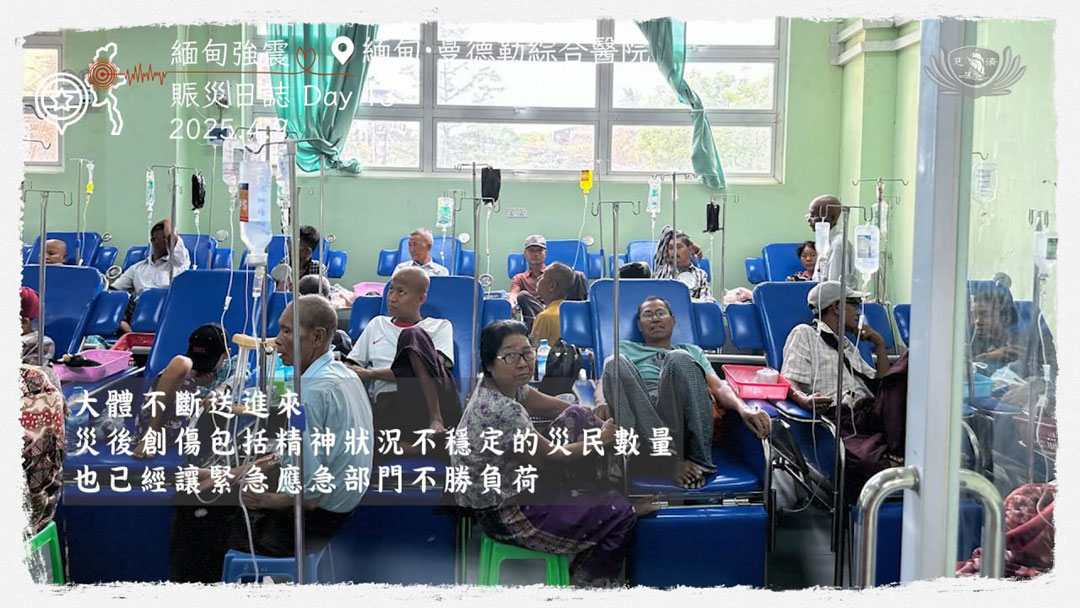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河水山区发生大火,烧毁了大片的亚答屋。住在靠近河水山的我们亲眼看到距离不远的河水山,熊熊燃烧的烈火有如火焰山,那火光和透过空气传过来的热度,使人惴惴不安、心有余悸。
大火过后,爸爸很快在红山区的金殿路租到了当时刚建好的政府组屋,于是便举家搬离Jalan Tiong一带的亚答屋,住进了金殿路的政府组屋。
我们住在金殿路的政府组屋,大牌12号,四楼,一房一厅组屋。房间有一张双人床,那是爸爸妈妈睡觉的地方,我和妹妹则打地铺,睡在床边的地上。再过去靠窗口的地方,摆了一张简陋的书桌,是我和妹妹温习功课的地方。
后来爸爸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很大的长方形的木柜,约1.2米高,宽0.75米,深45cm,那应该是人家托运货物的木箱,中间还分成两格,刚好就可以作为我和妹妹的书橱。我从小喜欢养鱼,还记得我在这“书橱”上放了一个鱼缸,养了几条金鱼。
在客厅中,正对着窗口的墙壁,摆了一张高约120厘米的神桌,那是当时一般神桌的高度。桌上摆着历代祖先的牌位,佛祖及观世音菩萨的神像。那是拜祭祖先以及每天祖母礼佛的地方。
客厅的大门在客厅的一侧,另一侧是一张单人床,那是祖母睡觉的地方。早年的政府组屋只有单房式、一房半厅式、一房一厅,最多也只有两房一厅。没有四房及五房式组屋。所以像我们一家五口,也就只能这样的挤在一房一厅的组屋里。不过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屋子住,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这栋组屋高9层,我们住在第4层。门外就是公共走廊,以铁栏杆围起来。祖母爱种花,就在栏杆下端摆了一整列花盆,种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花如芍药、月季、金银花、绣球花、龙船花、鸡冠花、茉莉花和千日红等。每天早晨和傍晚,她就会为花卉浇水、除虫、加肥。
我经常手靠着栏杆,呆呆看着组屋前面那深不可测的丛林。那是一片翠绿浓密的树丛,清晨时分,清脆的鸟啭宛如天籁,催促着人们起床;晚霞燃烧的傍晚,“咕啊呱……咕哇呱……”的蛙声一起一伏,揭露了丛林中的水世界。不论是有月光或只有星星眨眼的夜晚,“唧唧”的虫鸣如催眠曲,催促着人们早睡早起身体好。
而大白天树丛林中却经常传来“呜呜呜……”的汽笛声,而且还冒出一股黑烟,长长的如宣纸上一撇黑色的墨汁。这使年幼的我心中充满了好奇。后来有个机会进入这片丛林之中,我才知道原来那是火车。而丛林之中其实另有天地,有种菜的农民、亚答屋、菜园,还有一条穿过丛林的火车道。我和幼年的友伴经常走入丛林中,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这栋组屋走廊的尽头,一边是一个乡村,浓密的树丛中露出许多亚答屋;另一端是一个大草坪。草坪的四周围绕着许多政府组屋。我的一位姓欧阳的小学同学,住我们这栋组屋的侧面,有时候我就和他一起在草坪上学踏脚车。组屋的后面,住着另一位女性友人。再过去的一栋组屋,则是住着我的好友佐杰。小时候我喜欢音乐,但爸爸不喜欢我学音乐,我只好在佐杰家里学。他的爸爸是一名牙医,家里有风琴、二胡、笛子等乐器。
当时的金殿路,有许多私会党,经常因为争地盘而互相殴斗。我就曾经在走廊的尽头目睹私会党徒激烈的殴斗和厮杀,场面可说血腥和惊险。记得有一次两派人马手持武器激烈厮杀,一位手持两把巴冷刀的青年和一位手持扁担的青年互殴,持巴冷刀者不敌倒地,持扁担者趋前一棒朝他的胸口击打下去,想必肋骨尽裂。持扁担者随后还以扁担垂直往倒地者的胸口狠狠一击,我想他的心脏必已碎裂,回天乏术了。虽然事隔几十年,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迄今仍然历历在目。
60年代到70年代,新加坡有许多私会党,不过一般来说他们很少骚扰一般市民。只知道他们经常会向做生意的收取保护费,只要每个月给他们钱就没事了。但是因为他们有派别之分,有时会因为争地盘而互相殴斗。
这些私会党徒大多数匿藏在亚答屋区里,警方很难抓到他们。也因为这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新加坡政府开始有计划的建立起许多政府组屋,以代替容易发生火患的亚答屋。现在的新加坡,已经难得看到亚答屋了,在政府“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有接近9成的新加坡人,都住在政府组屋里。#